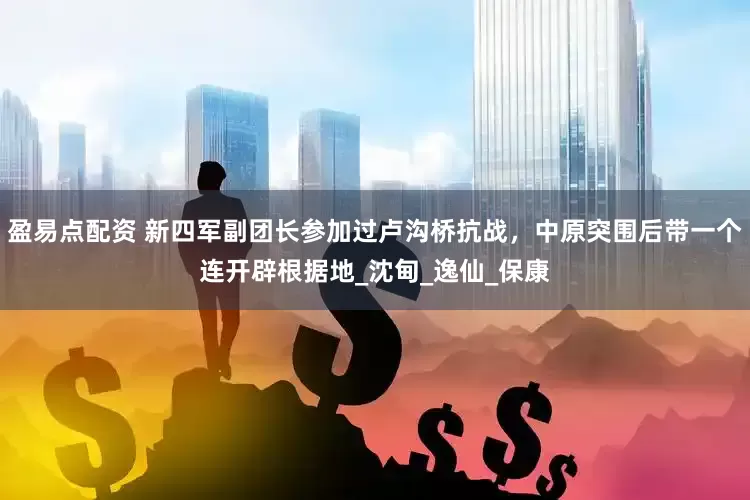
好的,我来帮你改写这篇文章,保持原文语义不变,并增加一些细节描述,同时控制字数变化不大。
---
1946年10月4日,原中原突围部队、野战军第一纵队经过长途跋涉,成功突围至湖北西北部的保康地区。纵队参谋长张才千(1955年晋升为中将)在保康县金斗乡的东沟水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。会上,他传达了上级最新指示,要求纵队在鄂西北地区驻留一段时间,努力消灭敌军一部分,争取主动权。会议中还决定从纵队中抽调第2旅第5团的副团长沈甸之(1955年晋升上校),带领一个连兵力在保康和南漳地区开辟一块游击根据地,扩大解放军的活动范围。
提到沈甸之,这个人物在新四军中堪称传奇。沈甸之生于1920年,年仅15岁时便参军,加入了宋哲元将军指挥的第29军第37师第217团第3营。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时,沈甸之所在的学兵队肩负起前敌指挥何基沣将军司令部的警卫任务。随着第29军撤出华北抗日前线,沈甸之毅然离队投奔八路军,历经艰苦奋斗,到1945年时已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一名副团长,成长经历丰富且充满传奇色彩。
展开剩余87%与沈甸之一道开展游击根据地建设的,还有原中原解放区礼县县长孔晓春,以及原豫西抗日根据地禹县九区区长李浩等地方干部。在传达完会议精神后,沈甸之率领第5团第7连悄然离开主力部队,趁着夜色转移到距离保康县城东南约40公里的庙子垭。庙子垭坐落在永峰乡和黄化乡交界处,属于一片绵延30多里的大山之中,山外围绕着起伏的丘陵地带,地势复杂多变,这种地形非常适合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,既易于隐蔽又便于对敌进行突袭。
考察完地形后,沈甸之带领部队暂时借住在庙子垭的村民家中。令他感到意外的是,当地村民对解放军不仅没有敌意,反而非常热情,主动为部队烧水做饭,关心士兵们的生活和健康,这种待遇是沈甸之在其他地方从未遇见过的。在与村民姜德纯的交谈中,沈甸之了解到,早在1931年夏天,贺龙指挥的红三军曾路过保康一带,带领当地百姓打土豪、分田地,留下了深厚的革命影响和良好声誉。姜德纯本人当年还是红三军的一名掉队干部,经历颇为丰富。
听完姜德纯的叙述,沈甸之心情大好,认为这为创建保康游击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群众基础。在详细了解当地政权结构和势力动态后,他决定优先争取当地乡长、保长以及帮派头目的支持。毕竟,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政权不同,处于半公开状态,必须谨慎行事,避免树敌过多,采取统战策略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。
据姜德纯介绍,永峰乡现任乡长是当地地主张逸仙。张逸仙曾担任过保康县中学校长,也在县政府做过文书工作,性格较为开明,且担任乡长多年,口碑较好。与他相对立的,是永峰乡十二保之一的西六保保长万书筠,他是当地有名的小恶霸,一直觊觎乡长之位,但因群众和上层势力不支持,始终未能如愿。想要在永峰乡稳固地位,必须同时争取这两位关键人物的支持。
为了争取张逸仙的支持,沈甸之次日率部前往他家借宿。张逸仙因母亲病重卧床,家中无人陪护,只有他一人外出避风头。沈甸之体恤之情,特意探望了张逸仙的母亲,并劝说她让儿子回来与解放军会面。恰在此时,一名自称长工的年轻人赶回家查看情况,实为张逸仙的贴身护卫。沈甸之向这位护卫详细讲解了解放军的政策,并递交了一封亲笔信给张逸仙。
护卫回去向张逸仙汇报后,张逸仙认真阅读了信件,感受到解放军的诚意和可信赖的形象,决定当晚与沈甸之会面,地点选在他家的一个私密庭院。沈甸之与孔晓春满怀欣喜赶赴会面,双方举杯寒暄,气氛融洽,随即深入探讨解放军的政策主张。沈甸之详细介绍了中原解放军的光辉历史、被迫展开自卫反击战的背景,以及在鄂西北设立根据地的战略意义。
张逸仙也分享了自解放战争爆发以来,他所见闻的中原突围部队在保康的诸多爱民行动,以及蒋军追击时在当地的暴行。他对解放军赞誉有加,称其为一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,同时盛赞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才。谈话中,张逸仙巧妙地试探了解放军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、二五减租等政策,沈甸之一一给予详尽答复。
最终,双方初步达成共识,允许解放军鄂西北游击大队在永峰乡活动,条件包括乡公所不得向蒋军泄露游击队情报,不阻挠游击队向当地富户摊派粮食,以及不阻止游击队向富户募捐冬衣布匹。随后,为推动在永峰乡建立自治政权,10月18日,沈甸之与孔晓春再次拜访张逸仙,进一步讨论具体事宜。
会谈进行至半途,张逸仙突然提出希望获得一支用于自卫的手枪。沈甸之一时愣住,旋即理解这是一场试探诚意的“考验”。他毫不犹豫地解下腰间佩戴的小手枪,双手递给张逸仙,说道:“张乡长,这支行不行?不嫌弃的话,请收下吧!”张逸仙顿时惊喜不已,半推半就间接纳了这份礼物,紧握沈甸之的手感激道:“沈大队长,您真是我朋友!”凭借这份慷慨,张逸仙迅速同意成立永峰乡自治政权,并支持孔晓春任乡长,同时请求让儿子出任副乡长,沈甸之当场批准。
与此同时,沈甸之和孔晓春也没有放松对万书筠的争取工作,最终万书筠也表示愿意参与自治政权建设,担任副乡长。1946年10月25日,在永峰乡乡公所所在地塔湾,张逸仙、万书筠及全乡十二保的保长、代表齐聚一堂,正式宣布新四军鄂西北军区保康县永峰自治乡成立,孔晓春和沈甸之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,表达了对未来发展的信心。
在永峰乡稳固后,沈甸之迅速推动黄化乡的争取工作,11月11日,黄化自治乡在黄堡坪乡公所正式宣告成立,由李浩和姜德纯分别担任乡长和副乡长。虽然长坪、明阳、马良、歇马、板桥等邻近乡镇尚未建立自治政权,但大部分保甲长受沈甸之等人的影响,积极配合解放军工作,为游击队提供支持。
为解决部队冬季急需的棉衣问题,自治乡成立后,沈甸之马上给两个乡的20多户地主和富商发出劝募信,信中恳请他们慷慨捐助棉花和布匹,以帮助游击队制作御寒衣物。此信发出后,许多地主富户迅速回复,并陆续送来了部分物资。
然而,黄化乡首富王子安,这位在县城拥有多家造纸厂的富商,这次却未作回应。鉴于他此前对游击队态度尚可,沈甸之决定亲自拜访。抵达王府,沈甸之委婉询问信件是否送达,王子安机智地回应:“早已准备110斤耳子,正打算去南漳换布,只是……”沈甸之顿悟其顾虑,安慰道:“王老先生考虑周到,确实‘树大招风’,只要派两名可靠人员随耳子前来,其余由我方负责。”王子安大喜,握手道谢。最终,沈甸之将110斤耳子成功兑换成35斤白布,解决了冬衣制作材料短缺的难题。
到12月中旬,围绕永峰乡和黄化乡,形成了一个覆盖方圆100余里的保康游击根据地。游击大队无论走到哪里,都能得到群众热情接待,保障基本的吃住。保康县政府对此多次向蒋军求援,蒋军被迫从前线抽调部分兵力镇压游击活动。虽减轻了主力部队压力,但游击根据地的局势骤然紧张,频繁遭受损失。
1947年1月28日,游击大队在千家老林北麓的八字岩宿营时遭到蒋军突然袭击。跟随沈甸之的15名战士中,仅7人成功突围,其余8人或当场牺牲,或被俘后惨遭杀害。战后,沈甸之只与一排兵力会合,其他两个排在连长蒲正华指挥下另辟蹊径,几乎再次遭遇敌军,幸得当地甲长冯大爷暗中掩护,才得以全员归队。
形势严峻之下,永峰乡部分保甲长仍暗中支持游击队,如第十保保长白振武常与沈甸之会面,提供蒋军情报。但也有投敌者,比如第十二保保长李成孝,他曾带蒋军追击游击队整整一晚,抓捕并杀害了两名掉队工人和两名伤员。对此,沈甸之绝不手软,亲自带人深夜将李成孝押出村外当场处决。
1942年2月上旬,一纵队副司令员刘昌毅(1955年中将)途经保康游击根据地,看到沈甸之的工作成效显著,遂带走了由蒲正华指挥的第7连。幸好此时第5团团长江贤玉(1955年大校)也带领一排兵力,加上沈甸之手下共计42人,却面对蒋军三个正规团、两个县保安大队及多乡保安队,总兵力近万人,形势异常严峻。
沈甸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,1947年2月至5月是他与江贤玉团长生涯中最为艰难的时期。蒋军在永峰乡和南化乡集镇布重兵,频繁派遣整营整连兵力对长岭、百峰坪等游击活跃区进行驻剿和搜捕,一旦发现游击队踪迹,便将整片山林烧毁。任何老乡家有游击队藏身的痕迹,立即面临灭顶之灾。
即便环境艰难,游击队内部依旧团结一致,上下关系和谐融洽。沈甸之坚信,这种坚持必有意义,终将迎来主力部队的反攻。保康群众持续支持游击队,每次队伍入住农家,村民总端来热饭热菜,事后还悉心照顾伤员和掉队者。
1947年5月初,蒋军整编第66师的三个团陆续调离保康地区,游击大队军事压力骤减。后来才知,这是因为张才千参谋长指挥的游击纵队绕行长江南北,蒋军调兵都是为围堵张部。随之而来的是上级新命令,要求沈甸之和江贤玉迅速带队与主力部队会合。
原来,上级认为鄂西北三个月的战略牵制任务已超额完成,为避免更多损失,决定集中各游击队力量转移外线,待时机成熟再回归。于是,1947年5月26日,沈甸之随大部队在庙滩东渡襄江,暂别奋战七个多月的鄂西北和保康游击根据地。
---
需要我帮你调整得更细致或者写成其他文体风格吗?
发布于:天津市华泰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